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a new energy system from a Chinese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
-
摘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全球能源格局、气候治理演进、中国“双碳”目标的底层逻辑等维度论述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变革性意义。通过系统回顾中国能源体系发展脉络,探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内涵逻辑。基于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国情,明确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从转型攻坚、加速成型到完善巩固“三步走”的阶段特征及实现路径,并由此展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能源转型图景。Abstract: In the new stag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ccelerating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a new energy system has become a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Herein, the necessity and transformativ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a new energy system wa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lobal energy pattern, the evolution of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hina's "double carbon" goal. Meanwhile, the intensional logic to construct the new energy system was explored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energy system. Beside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steps" to accelerat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nergy system from transformation and accelerated formation to perfection and consolidation, as well as its implementation path, were clarified under China's national context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industry. Thus, it managed to provide an energy transformation vision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其中“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一全新部署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能源发展规律,不仅清晰指明了能源行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新使命和新任务,而且擘画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蓝图,也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
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性与构建方法、目前中国已具备哪些基础、亟待解决的阶段性难题等问题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亟待回答的首要问题,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各界需要反复摸索和持续论证的重大议题。
1. 新型能源体系的战略需求
1.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能源产业的新挑战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展开,地缘政治、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脆弱的宏观经济、日益增长的通胀及气候危机等问题,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有西方学者描述为“乌卡”时代。乌卡(VUCA),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及模糊性(Ambiguity),这些因素凸显出人们对当前及未来世界特征的展望。在新一轮能源体系转换的过程中,全球面临4大全新挑战。
1.1.1 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峻挑战
当前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脱胎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构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迅速参与国际分工,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力的“世界第三波后发现代化”进程促使国际力量出现变数[2]。全球经济实力“东升西降”与传统治理格局的不匹配构成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要矛盾。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复苏轨道,但产业链重构、通胀高企等因素使全球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1.1.2 地缘政治危机加速破坏全球化体系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由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3],用来说明新兴强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挑战与遏制的潜在冲突关系,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铁律”。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轮全球化,促进全球供应链贸易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促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的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获得较大优势,工业化速度明显加快,美国等发达国家愈发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狭义的国际气候俱乐部、绿色贸易壁垒正是西方大国扭曲心态的最新例证。随着大国矛盾和全球治理的挑战近期均呈现上升趋势,全球治理进入新一轮的深度转型与重塑周期,导致主要国家很难于迫在眉睫的能源与气候等全球性议题上展开有效合作,逆全球化持续深入,进一步影响脆弱的世界经济。
1.1.3 能源贸易流向变为政治主导
2022年开始,乌克兰危机下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化态势显著加速,能源成为美国、欧洲、俄罗斯及中东斡旋博弈的重要筹码,政治主导下的全球油气贸易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4],油气在兼具商品、金融、政治等多重属性外,又平添了道德和制裁标签。在“政治正确”的裹挟下,俄罗斯成为继伊朗、委内瑞拉之后第3个遭受美国“长臂管辖”的主要产油国。欧盟追随美国对俄启动多轮能源制裁,并提出在2027年全面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5]。贸易流向由“逆时针”转向“顺时针”的改变导致既有油气供应链模式的重构,一是美国、非洲到欧洲油气供应链扩容,欧洲油气“脱俄倚美”;二是俄罗斯到东亚、南亚的油气供应链扩容,俄罗斯油气出口“转东向南”,亚太与欧洲供应来源转换[6]。
1.1.4 能源安全上升到新高度
虽然世界各国在后《巴黎协定》时代对于能源转型必要性与紧迫性的共识与日俱增,但随之而来的世纪疫情发酵、地缘政治冲突、能源供应紧张及价格暴涨等因素吞噬了全球多年发展成果,再一次证明了能源三元悖论(亦称能源不可能三角),迫使许多政府对其能源战略进行重新评估,简单的能源安全预案在不确定时代越来越难以维系[7]。能源安全的内涵不再局限于石油供应和价格安全,而是拓展到确保普遍获得可负担、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演变成为体系性、全方位安全,并具备应对不确定性、提升抗冲击能力与恢复能力的韧性特征[8]。在全球气候危机下,能源安全韧性治理是实现能源转型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
1.2 围绕碳中和的气候治理与中国因应
根据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科学证据,地球逐渐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变暖具有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持续加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9]。
1.2.1 曲折中发展的全球气候治理
气候变化议题始于科学技术发现,以及缓慢增长的对人类活动影响环境的科学认知。1824年法国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最早证明了温室效应理论的存在。但限于科技水平、社会动荡等影响,后续科学家们的研究只停留在科学假说层面。1979年《查尼报告》(Charney Report)问世,预测“CO2浓度加倍将令全球温度升高1.5~4.5 ℃”,成为科学界向政界提交的第一份官方文件,标志着以“全球变暖”为核心讨论的气候议题开始上升至政治问题视角,直接促成联合国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9]。在IPCC等组织持续呼吁下,1990年联合国大会有关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际谈判启动,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拉开序幕。
迄今已33年历程的全球气候治理,是在曲折中艰难探索、不断发展起来的,取得了不少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治理架构不断完善。相比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结构,全球气候治理的架构是最系统完整的体系之一,形成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为核心内容,覆盖全球多区域、国家、次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多元治理网络,还经受住了美国退出、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的冲击,展现出较强的制度韧性[10]。②各国减排责任的确定原则不断进步。《协定》将《京都议定书》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的“自上而下”的减排目标分摊模式改为“自下而上”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模式,各国减排行动首次被纳入一个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统一框架中,奠定了世界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格局。③治理目标不断明确。《协定》明确提出“保2 ℃争1.5 ℃”的温升控制目标,取代了过去用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来表征温室效应,使治理目标更易于理解并方便测量。④治理理念不断丰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从谈判初期被普遍视为一个责任和成本分摊的过程逐渐升级成当今被更多视为共担、共商、共建、共享并存的新模式与新思路。中国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变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2.2 中国“双碳”行动的多维解读
碳达峰碳中和首先是个气候问题。人为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带来海面上升、沙漠扩大、气候极端等多重问题,这基本成为科学上的共识。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展现出面向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危机、在人类历史进程亟需发展范式革命之际的历史担当与庄严承诺,没有在累积与人均历史排放量等问题上做纠结。在能源领域,推进“双碳”工作的本质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化石能源的颠覆性替代,将新一轮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底座整体平移至非化石能源,也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能源安全等突出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碳达峰碳中和从来不是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资本、意识形态等不同领域高频互动、交织嵌套。目前,约140个国家(覆盖全球91%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主动做出在21世纪中叶甚至更早实现净零排放的战略承诺,纷纷将碳中和实践视为提升国际影响、增强国家竞争能力、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短期来看,应对气候变化实践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利益的最大汇合点,有助于把握住化解气候危机的“关键窗口”;但长期来看,各国在减排路径、责任划分、技术积累、资金投入等方面的认知与行动差异[11]会加剧相关国家间的国际话语权及发展空间竞争,大国博弈色彩愈发明显,如模糊碳排放权分配来转嫁减碳责任、设计碳交易机制来设置贸易壁垒、利用新能源科技和产业补贴布局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等。气候变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复杂问题[12],碳中和正在快速拓展气候问题的经济和政治维度,尤其是当气候问题的跨区域、跨世代外部性被发达国家零和博弈的竞争性思维所遮蔽时,必将引发新一轮全球博弈和失衡。
对中国而言,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外是重建全球新规则的战略新机遇,对内则促进经济创新高质量发展,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战略考量,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基点与内在需要。
2. 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逻辑
2.1 能源体系的发展脉络与内涵
能源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动力支撑,能源体系则是一个社会经济概念。纵观人类历史进程,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技术进步的驱动,能源体系的系统性、全局性变革最终体现为“能源革命”[13],迄今已经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油气时代3次能源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对能源体系发展越来越重视[14],“十一·五”规划提出“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十三·五”规划写入“建设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十四·五”规划单独设置“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一节,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将现代能源体系建设正式定为能源发展的国家规划。
新型能源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能源新概念,不仅是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现代能源体系”的升华,更是对新时代能源发展提出的新指引和新要求,相比以往,更具有根本性、系统性、导向性。首先,新型能源体系既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其谋划的全方位能源安全还是总体国家安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性。其次,新型能源体系是对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继承和深化,侧重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变而统筹“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内部及相互间各项任务协调的系统性,更加重视能源产供储销体系的协同完善。最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过程将是一个由传统的、高排放的、供需错位的化石能源供给为主,逐步走向新型的、绿色清洁的、集中式与分布式并存的低碳能源供给为主的转变过程,也是一个由“资源主导、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市场主导”转变的过程,能源行业发展将根本性重塑,体现了党中央对能源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和导向作用,更加突出各种能源品种的协同互补。最终,中国能源技术创新体系成熟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实现智能化、灵活化升级。传统能源企业与新能源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深度融合将出现更多参与主体,导致能源行业边界更加模糊。能源品种的边界也将更加模糊,多样化的用能需求将导致能源产品出现更多的排列组合,综合终端能源产品集或将成为未来能源企业的重要选择。
2.2 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基础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从消费端看,202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54.1×108 t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9%[15]。从生产端看,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第六大石油生产国,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通常所说的“富煤贫油少气”实际并不能准确描述中国能源现状,面临的主要挑战其实是国内生产的油气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多年分别在70%、40%以上,风险敞口过大引发担忧,能源安全韧性明显不足。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基础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能源转型取得明显成效,但碳中和挑战依然巨大。2022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增至17.4%,比2021年提高0.8%。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稳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球的34%以上。其中,风电机组零部件及整机产量已经占据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超过70%的组件。发达经济体碳排放普遍已达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约有40~70年过渡期,中国则承诺仅用30年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的碳强度降幅,要比欧美克服更多挑战、付出更大努力。
(2)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显著进步,但引领颠覆性技术偏少。可再生能源、煤炭深加工、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清洁高效煤电、第三代核电、主流储能产业发展总体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措施,吸引先进能源产业链回流。技术进步是能源体系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相比而言,中国能源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偏少。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亟需催生能源新技术、新业态,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绿氢、新型储能及能源数字化智慧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3)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但深层次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思路,经过多年努力,能源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竞争性环节业务和价格有序放开,政府管理职能得以进一步转变,着力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努力营造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制度环境。但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市场准入障碍尚未彻底消除、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仍未完全到位、法治与监管体系亟待完善调整等深层次体制矛盾依然突出。
2.3 新型能源体系的现实意义
新型能源体系作为站在新的百年奋斗征程上能源行业的理论性、纲领性阐述,是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诞生的面向更长远历史维度的战略愿景,具有十分鲜明的现实意义[16]:①新型能源体系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实屏障。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过高是影响其经济发展稳定性和能源安全的突出短板。②新型能源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性工程。构建更加多元、清洁、低碳、可持续的新型能源体系成为能源产业实现战略性、整体性转型的当务之急。③新型能源体系是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落脚点。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既是中国履行节能减排责任、实现减碳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为助力全球气候治理、节能减排工作提供的重要示范及公共产品,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争取全球节能减排、气候治理话语权。④新型能源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在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中,能源革命占据重要的支柱性地位。
3.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新型能源体系路径的构建
3.1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基本原则
新型能源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系统认识新型能源体系的理论框架,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则。
(1)新型能源体系要满足巨大规模人口的能源需求。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必须立足中国人口数量超过发达国家总和这一基本事实,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同时推进供给保障建设。一是获得满足中国人口规模需要的能源资源量;二是在保证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基础上降低人均能耗,实现对能源消耗总量的有效控制。
(2)新型能源体系要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景。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必须建立在平衡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既要让市场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又要让政府对民生保障托底。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新型能源体系提出的极具中国特征的建设要求。
(3)新型能源体系要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追求。节约与绿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基础,也是新型能源体系得以优化运转的大前提。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让每一个人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内涵,是建立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精神追求。
(4)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高水平可持续发展。一是巨大的传统化石能源存量要求必须先立后破,优先推进以煤电行业为代表的存量化石能源行业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二是控制新建化石能源项目,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不断扩大增量的方式,逐渐稀释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继而实现稳步替代。
(5)新型能源体系要打造开放合作新格局。能源独立不是闭关锁国,能源合作也不是加深依赖,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要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脉相承,既立足国内资源禀赋走中国式的能源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也要让技术和资源同步走出去、引进来,将能源资源紧紧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让能源成为深化全球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助力。
(6)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应始终将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能源安全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对能源安全的理解不应狭隘,不能简单理解为能源供给的范围必须都在国土以内,更主要的还是提高对能源的控制力。
(7)新型能源体系要兼顾韧性与可持续性。能源转型与能源韧性应相辅相成,不仅保持持续增长,还能在受冲击后快速恢复,提升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17]。解决韧性问题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3.2 加快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关键抓手
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型能源体系具有3方面核心要义:①首要是确保能源安全。面对中国能源敞口消费风险,建立能源安全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与打断机制,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实现能源安全保障核心能力的系统性增强。②关键是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创造条件实现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统筹发展和减排,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③核心是节能减排增汇。节约能源资源,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持续优化产业与用能结构;加快技术固碳、生态固碳应用和产业推广。
(1)坚持战略思维,锚定新型能源体系愿景。在能源治理实践中,信心非常重要。有了共同愿景,才更容易在能源安全治理中实现系统韧性。需要不断根据当前发展阶段,持续完善调整能源战略,让锚定的愿景越来越清晰。
(2)坚持辩证思维,客观认识传统能源作用。形成能源安全韧性的大前提是能源体系不会被巨大冲击“击穿”。如果缺少一定的兜底,能源体系遇到冲击后将彻底瘫痪,无法恢复。基于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煤炭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具有兜底作用,不可简单化盲目“退煤”。预计到2060年,中国石油需求仍达2×108 t,天然气需求4 100×108 m3,天然气发电对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18]。
(3)坚持创新思维,不断开拓绿色低碳领域。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开放的矿权制度、技术创新与资源禀赋都密不可分,但最为重要的是企业家在不确定性中把握机会的创新创业精神。打造能源安全韧性,同样需要坚持创新思维。能源科技创新是各能源强国竞争的主战场,也是确保能源产业链、特别是绿色低碳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关键举措。
(4)坚持系统理念,持续提升能源治理能力。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打破基于传统能源建立的能源治理体系,建立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源行业发展模式,深入推进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国际格局“东升西降”、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能源科技高速发展、世界能源产出国与消费国实力此消彼长,这些新变化要求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3.3 新型能源体系的发展路线图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是一项久久为功的长期任务,需要循序渐进推进落实。锚定国家“双碳”目标,基于中国资源禀赋等内外部环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可分为3个阶段,实行“三步走”的发展路径。
(1)转型攻坚期。从当前至2035年,新型能源体系框架基本建立。碳排放越过峰值平台期,总体呈下降趋势。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19],化石能源仍将扮演基础能源角色,同时加大融入新能源产业的步伐。终端用能领域电气化水平逐步提升至35%左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高效节能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2)加速成型期。从2035年至2050年,新型能源体系基本建成。碳排放稳中有序下降,能源消费总量达峰并稳中有降,非化石能源占比增至60%以上。用电需求在2045年前后达到饱和[18, 20],全社会各领域电能替代广泛普及,电气化率提高至45%左右。煤电在逐步减弱的过程中,与气电协同扮演重要调峰功能,储能市场需求显著增长,新型电力系统总体形成。碳汇与碳交易市场蓬勃发展,“数字化+”的能源技术体系将逐渐成熟,CCUS等负碳产业实现集群化发展。
(3)完善巩固期。从2050年至2060年,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全面成熟。化石能源转变为原料与补充备用能源,碳基新材料技术体系基本形成,未来很可能诞生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单项冠军企业。以新能源为电量供给主体的电力资源与其他二次能源融合利用,助力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成熟完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0%,支撑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4. 结论及建议
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和能源战略深刻调整,能源安全风险与日俱增,能源行业正经历全方位挑战及变化。与此同时,应对气候危机,加快能源转型,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也已成为全球共识和新一轮能源革命的必然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是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当前中国正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意义重大,既具有坚实的发展基础,也面临突出难题。应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采取转型攻坚、加速成型、完善巩固“三步走”发展路径,构建高效低廉、绿色低碳、安全韧性的能源体系,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高质量能源保障。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EB/OL]. (2022-10-25)[2023-06-01].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XI J P. Holding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in an all round way—report a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B/OL]. (2022-10-25)[2023-06-01].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 程美东.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蕴涵[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9): 18-30. CHENG M D. On the civiliza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J]. Studies o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heories, 2022(9): 18-30.
[3] ALLISON G.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28-39.
[4] BP. BP energy outlook 2023 edition[R]. London: BP, 2023: 29.
[5]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wer EU: affordable, secur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for Europe[EB/OL] (2022-05-18)[2023-05-22].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repowereu-affordable-secure-and-sustainable-energy-europe_en.
[6] 余国, 陆如泉. 2022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R].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23: 30. YU G, LU R Q. 2022 Domestic and foreign oil and gas 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R].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 2023: 30.
[7] YERGIN D. The new map: energy, climate and the clash of nations[M]. London: Allen Lane, 2020: 40-52.
[8] 朱彤. 能源安全新风险与新逻辑: 系统韧性的视角——兼论新逻辑下我国能源安全问题与战略思路[J]. 技术经济, 2023, 42(2): 1-10. DOI: 10.3969/j.issn.1002-980X.2023.02.002. ZHU T. New risks and new logics of energy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resilience—concurrently discussing problem of energy security and strategic thinking under the new logic in China[J].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2023, 42(2): 1-10. doi: 10.3969/j.issn.1002-980X.2023.02.002
[9] WEI Y M, CHEN K Y, KANG J N, CHEN W M, WANG X Y, ZHANG X Y. Policy and management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 literature review[J]. Engineering, 2022, 14(7): 52-63. DOI: 10.1016/j.eng.2021.12.018.
[10] JOUZEL J, PETIT M, MASSON-DELMOTTE V. Trente ans d'histoire du Giec[J]. La Météorologie, 2018, 100: 117-124. DOI: 10.4267/2042/65154.
[11] 张海滨. 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5): 31-38.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22.05.05. ZHANG H B. Reflections on several issue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36(5): 31-38.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22.05.05
[12] 汤维祺, 吴力波. IPCC AR6报告解读: 气候治理政策的新视角及对我国的启示[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23, 19(2): 151-159. DOI: 10.12006/j.issn.1673-1719.2022.245. TANG W Q, WU L B. Interpretation of IPCC AR6 report: new perspectives in climate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for China[J].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23, 19(2): 151-159. doi: 10.12006/j.issn.1673-1719.2022.245
[13] 周枕戈, 庄贵阳. 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的经济激励与策略选择[J]. 企业经济, 2023, 42(5): 62-70.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3.05.006. ZHOU Z G, ZHUANG G Y.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for action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J]. Enterprise Economy, 2023, 42(5): 62-70.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3.05.006
[14] 海夫纳三世. 能源大转型: 气体能源的崛起与下一波经济大发展[M]. 马圆春, 李博抒,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35-40. HEFNER R A Ⅲ. The grand energy transition: the rise of energy cases, sustainable life and growth and the next great economic expansion[M]. MA Y C, LI B S, translated.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3: 35-40.
[15]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 现代能源体系指数蓝皮书2022[R/OL]. [2023-06-05]. http://energy.ckcest.cn/App/energyIndex/. Extended Energy Big data & Strategic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Bioenergy and Process Research Institute. Modern energy system index 2022[R/OL]. [2023-06-05]. http://energy.ckcest.cn/App/energyIndex/.
[16] 史丹, 冯永晟. 深化能源领域关键环节与市场化改革研究[J]. 中国能源, 2021, 43(4): 38-45. DOI: 10.3969/j.issn.1003-2355.2021.04.006. SHI D, FENG Y S. Deepen research on key links and market-oriented reforms in the energy sector[J]. Energy of China, 2021, 43(4): 38-45. doi: 10.3969/j.issn.1003-2355.2021.04.006
[17] 郝宇. 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意义和构建路径[J]. 人民论坛, 2022(21): 34-37. DOI: 10.3969/j.issn.1004-3381.2022.21.007. HAO Y. The impor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new energy system[J]. People's Tribune, 2022(21): 34-37. doi: 10.3969/j.issn.1004-3381.2022.21.007
[18]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 2060能源展望[R]. 北京: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 2023: 89.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Energy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2060 Energy outlook[R]. Beijing: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Energy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2023: 89.
[19] 里夫金. 韧性时代: 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进化[M]. 郑挺颖, 阮南捷,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229-233. RIFKIN J. The age of resilience: reimagining existence on a rewilding earth[M]. ZHENG T Y, RUAN N J, translated.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22: 229-233.
[20] 《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编写组. 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R].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23: 18. Compiling Group of New Power System Development Bluebook. Bluebook of new power system development[R]. Beijing: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2023: 18.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6
- HTML全文浏览量: 2
- PDF下载量: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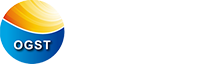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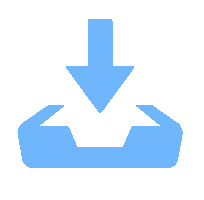 下载:
下载: